獨家:50億背后,大眾和小鵬是怎么合作的
汽車商業評論 | 03-14
 23892
23892

撰文 / 張霖郁
設計 / 琚 佳
2023年4月17日,上海車展前一晚。
大眾中國在位于場館不遠的上海外灘國際電競文化中心舉辦“大眾之夜”,當晚的重頭戲是旗艦車型純電ID.7。這款車僅是亮相,尚未量產。

一汽-大眾計劃當年年底上市,上汽大眾原計劃緊跟此后。
當晚或準確地說是當年,所有合資傳統車企產品和傳播都及其虛弱,既沒有新勢力的科技感也無新勢力的話題。
那天的活動現場布置,展示了ID.7的安全、環保,座椅的人體工學,勉強智能的輔助駕駛,再沒有能與大眾在華江湖地位匹配的亮點。而另一邊,新勢力正演示他們先進的智駕與智艙。

當晚發布會結束,展臺上的兩臺ID.7被觀眾例行包圍,這款車是基于MEB平臺的純電車型,從外觀到內飾,和之前的ID系列差別不大,很多觀眾看完后便離場。
在場的一位德國籍汽車行業專家告訴汽車商業評論,ID.7之后的量產版外觀和內飾南北大眾還會各自調整,但整體無法做太大改動了,“MEB平臺的車只能是這樣”,這位專家說。
這款車最終在一汽-大眾的佛山工廠下線,定價20萬元以上,銷量至今慘不忍睹,上汽大眾則最終放棄了這款車的量產計劃。

那晚結束后的第二天,在各種新車型的發布以及國外高層組團來訪、中國車企崛起的聲浪縫隙,大眾中國官網悄然發布了“投資10億歐元在合肥成立一家名為‘100%TechCo’的科技公司,這家公司功能是整車研發、零部件研發以及對應的采購業務,新聞稿中還提及開發周期將縮短30%。
很長一段時間,很多業內人士不知道這個“100%TechCo”究竟是干什么的,和早一年成立的軟件開發公司CARIAD中國有什么區別。
今天回頭看,大眾在華真正的變革是從100%TechCo成立這天開始的。
大眾集團于當地時間2025年3月11日發布了2024年財報。整體銷售收入實現3247億歐元,同比微增0.7%,去年銷售收入為3223億歐元。
營業利潤為191億歐元,同比下降15%,營業利潤率為5.9%。據大眾集團表示,營業利潤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固定成本的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凈額達26億歐元的特殊支出,主要用于企業內部重組。2024財年凈利潤124億歐元,同比下降30.6%。

經過數次危機當下的大眾集團,在全球各區域市場都在逐漸轉身,兩年前制定的戰略正展露成果,中國市場同樣如此。
德國終于開放本土自研
“100%TechCo”全稱是大眾汽車(中國)科技有限公司(簡稱VCTC),當時的CEO是韓鴻銘(Marcus Hafkemeyer),他也是大眾中國CTO。
2024年1月底,也就VCTC宣布成立后的第9個月,吳博銳(Thomas Ulbrich)接替韓鴻銘,擔任VCTC掌門人以及大眾中國CTO,韓鴻銘則調去CARIAD中國和地平線的合資公司酷睿程擔任CEO。

吳博銳(Thomas Ulbrich)
德媒Handelsblatt在2022年的一篇報道里這樣形容吳博銳,“他在大眾集團有故障排除專家的聲譽,無論哪里出問題,哪里陷入停滯,哪里軟件未能按時完成,他都會介入。”2022年,他正要出任大眾品牌成立的“新移動”業務負責人,這一項目包括大眾品牌純電車型以及軟件兩大業務。大眾MEB平臺也正是他主導開發的。
吳博銳這次被派往中國“救火”,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平臺以及軟件主導能力,另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自己分別在上世紀90年代和2010年前后,在一汽-大眾和上汽大眾任職,當時從采購做起,對中國整個供應鏈以及生態有實戰經驗。
VCTC是大眾集團在德國本土之外最大的研發中心,也是大眾在華40年來首次真正放權給本土團隊。
VCTC有了本地研發決策權,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能在中國市場自研是多讓人興奮的事嗎?多少人多少年都想這么干!他們都沒實現……中國人可以在本土研發自己的產品了!”一位華人軟件工程師談到這一話題時流露了他的興奮。
這里需要提到的是,吳博銳掌舵VCTC的任命官宣一個月后,CARIAD中國CEO也同時換了人,原CEO常青由韓三楚接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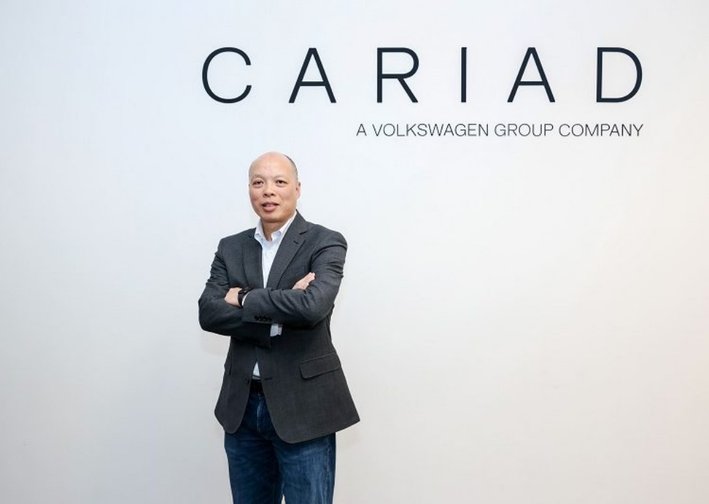
韓三楚
韓三楚在2021年出任長安首席軟件架構師,當時帶領2000人團隊開發了SDA架構,這個電子電氣架構是國內真正意義上第一個區域控制+中央計算的架構。他和團隊當年開發時間為兩年半。
他2024年6月底在北京CARIAD的員工大會上提出了“One Team”的概念,當時CARIAD中國的組織架構即將調整。
他說,之前每個人做一小塊業務,以此職責為邊界,但之后VCTC、CEA將成為一個團隊,不分哪個公司哪塊業務,大家跨部門一起做。
當時他對于要進入CEA開發業務人員的要求是“必須是真正有代碼能力的軟件工程師”,這是硬指標,CARIAD中國內部還進行了代碼測試,他本人也參加了這一測試。
VCTC和CARIAD是大眾集團的兩個平行部門,聯合承擔了CEA的開發工作,而CMP平臺則由VCTC負責開發。
隨著CARIAD之前幾年在德國的拖延表現,很多內部人士質疑這一部門獨立的必要性。
但2024年財報會上,大眾集團CEO奧博穆(Oliver Blume)在QA環節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說CARIAD仍將繼續其獨立地位,它承擔著PPE平臺以及電子電氣架構E3 1.1和E3 1.2的開發、更新升級以及適配等任務。
對于吳博銳和韓三楚而言,他們的首要任務是交付CMP+CEA,交付時間即在今年。這一任務他們在接任時就非常清楚。
這一套新平臺和新架構的組合將給大眾中國在華2026年以及2026年之后的車型帶來質的變化,與新勢力之間的差距將大大縮短。
另外,VCTC作為中國研發決策中心的另一個證明是,自吳博銳接手后,位于合肥的工廠大眾安徽(簡稱VWA)原下設的研發部門也直接并入VCTC旗下。
VCTC可以說是大眾在華的核心組織,它同時對接了一汽-大眾、上汽大眾和大眾安徽研發相關的統籌、標準制定以及相應的采購業務。
CEA架構進展
2月21日,大眾中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貝瑞德(Ralf Brandstaetter)到合肥查看CEA的進度。
內部人員告訴汽車商業評論,他來的前一天,吳博銳、韓三楚以及各業務的高級經理檢查各環節到很晚,確保第二天的演示無誤。
貝瑞德那天其實是先到辦公室和員工例行講話,之后下樓去看了成果,然后他意外地再次回到樓上,站在了小柜子上對大家表示感謝。這一幕后來傳到網上,很多人都看見了平常具有德式理性的貝瑞德“站上了桌子”。

“當時大家都很激動,架構團隊也很激動”,一位在現場的工作人員告訴汽車商業評論,“但之后我們很快就忙著解決后續問題了,來不及多激動”。
據汽車商業評論了解,目前CMP搭載了CEA的測試車已完成相應的測試,包括冬測,后續新的功能,將通過OTA的方式來迭代更新。
CEA由VCTC和CARIAD中國聯合開發,目前團隊共有900多人,VCTC和CARIAD中國的人員比例在55:45左右,之后團隊人數還會增長。
從吳博銳再到韓三楚的入職時間看,大眾中國給他們的研發時間差不多就一年,但韓三楚當時在長安帶著2000人還用了兩年半時間。
據CARIAD中國內部人士告訴汽車商業評論,VCTC和CARIAD中國兩個團隊合在一起準備著手開發CEA時,已經是2024年7月了。
貝瑞德那天看到的成果,其實是兩個團隊還不到一年所實現的進展。
這里不得不提到小鵬。
大眾汽車是在2024年2月官宣與小鵬簽署平臺與軟件聯合開發技術合作協議,2個月后,大眾集團宣布與小鵬共同開發基于區域控制及準中央計算的電子電氣架構。大眾以月費的方式支付這一合作。
這一時間節點似乎都緊貼著吳博銳和韓三楚的入職時間。
小鵬在這次合作上保持敞開,他們把自己EEA架構的軟件代碼開放給大眾的CEA團隊,這大大縮短了整個架構的開發時間。
但事情并不是這么順利。
2024年7月,VCTC和CAIRIAD開始組隊開發CEA時,因內部人員構成不同,有人是一汽-大眾的軟件工程師,有的是上汽大眾的,有的是德國外派過來的工程師……大家的理念、背景、工作習慣甚至語言都不同。
“剛開始的磨合非常痛苦”,一位內部人員告訴汽車商業評論。
這一痛苦磨合的根源之一是中國本土首次被授權自研,在流程以及決策過程不再是以往大家習慣的一套方式。因為之前都是全球車型、全球平臺、全球架構,這些在德國已完成,到了中國,只需依據既有流程做就可以了。
但CEA現在的開發方式,之前沒有這樣的模板和規程,大家沒有現成的流程和經驗可循。所以部門和部門之間會有業務邊界的沖突、決策上的模糊地帶、資源資金如何分配等一系列問題。
據汽車商業評論了解,吳博銳最終決定每天早上,固定用半小時來處理這些問題。
每個人每個團隊,不管你職級是什么,如有爭議或需要決策,都可以提出和他開會。但前提是提出者也需要做好相應充分的書面準備來討論。與會者不需全員,涉及這一話題的員工都能參與。
他來判斷和決策。
“周一到周五,每天如此。這個其實對他精力的消耗很大,因為他還有很多其他事情。但這么做,加速了整個流程。如果按著以前大眾的流程,一件事情兩個部門扯皮,走流程,一直就沒有處理,很多事情只能擱置,效率極低。這里不一樣,你今天早上申請個硬件,開發用,下午就到了,多爽啊!如果是以前的話,有可能要等幾星期。”一位在大眾體系十年不到的資深管理層告訴汽車商業評論。
快30%
大眾在2023年成立VCTC時,就提出純電新車型的開發周期要縮短30%,這是和基于MEB平臺的開發時間相比。
據汽車商業評論了解,CMP平臺和MEB通用性不大,更多是一個成本導向的A級車平臺。
傳統大眾集團的開發流程是市場有需求或準備開發某一類新車時,研發部門需先開發平臺。他們開始對平臺進行各種維度的定義,之后再拿著去給各個品牌開發車型,各個品牌就去設計外造型和內飾,等這兩樣設計好了,然后做油泥模型,這個時候,外造型沒定之前,下車身是無法提前測試的。對于底盤的測試需要等到外造型和內飾完全做好之后才能測試。
這些流程一環扣一環,后一環節須等到前面的環節完成后才能進行。
據VCTC的內部人員告訴汽車商業評論,現在他們的開發方式不同了。
下車身的平臺、電子電氣架構以及智駕和智艙可以單獨測試,這些可裝在其他的車殼子下面。他們不用等到外造型出來,便可單獨測試。研發團隊通過VR技術做虛擬的硬件設計,進行車身的硬件設計以及調教和校準。
設計團隊可同步進行外造型和內飾設計,下車身的研發與測試也同步進行,兵分兩路,最后合在一起。這一流程大大縮短了時間。
“每一測試環節都仍是大眾標準,時間雖然短了,但安全品質沒有受到影響。”一位工程師說。
研發能加快30%的另一個原因是研發授權本地決策后大大縮短了決策和以及反饋周期。
即將開始的上海車展,大眾中國此次將在大眾之夜亮相AUDI品牌首款量產車型、基于PPE純電動平臺的奧迪車型、CMP平臺首款概念車以及首款增程式車型。
2026年,大眾在中國市場至少有6款純電車型上市,大眾安徽就是金標大眾也將推出兩款B級車。
據汽車商業評論了解,這些車型已陸續在量產階段,有些功能已完成交付。這是大眾的中國速度。
3月5日,大眾集團在德國亮相了一款純電小車ID.EVERY1,這款車是基于MEB平臺,售價在2萬歐元,預計2027年于歐洲上市。
在3月11日舉行的大眾集團2024財報會上,奧博穆提到中國速度和中國成本都將應用在這款車上。
大眾和小鵬是怎么工作的
“和小鵬的合作,一開始預測兩個團隊磨合會比較困難,實際上挺順利的。”一位CARIAD中國的管理層告訴汽車商業評論。
據汽車商業評論了解,CARIAD中國共派出200名員工,VCTC也派出了自己的員工去廣州小鵬總部學習。
人員是分批次去的。
“他們對我們很敞開,給了單獨的一塊辦公區域,我們是一對一貼身跟著他們學的,看他們的代碼怎么寫”,一位去了廣州的內部人員告訴汽車商業評論。
期間大眾的軟件工程師寫完自己的代碼后,會和小鵬團隊的人一起檢查這些代碼。
然后小鵬的工程師出題考試,大眾的工程師來答題。這些都是非常嚴肅的流程,期間大眾的軟件工程師在答題時都很緊張,因為這會直觀反饋你的學習以及代碼能力,也會反饋到直接主管那里。
等考試結束后,大眾的軟件工程師需把學到的軟件代碼能力直接應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化為自己的能力。
“等后來看懂小鵬的代碼后,我們竟然也會開始挑刺了”,這位內部人員說。
2024年北京車展上,何小鵬在被問及與大眾似敵似友的關系中,如何看待小鵬做到的這種開放?
他說:“一家車企全球通吃是不太可能的。我需要找一家全球強大、原來有底蘊的公司,能夠讓我們向他們學習,剛好我們也有一些能力,他們也有需要,我是這樣的想法,即使在局部上有一點的沖突,但從終局戰略上,是沒問題的。當你有了這個想法后,就不會太在意,你就會開放大家所需要的事情,我是非常愿意開放地和大眾一起往前走的,這樣才能足夠信任。”
除了小鵬,大眾還有地平線以及中科創達這兩家中國合資伙伴來實現與國內友商齊平的智駕和智艙能力。
“大眾品牌從基因上,從沒宣稱過自己是技術的領先者,這一點大家要客觀。我們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做出CEA,和原來的大眾相比,已經很快了,但我們正努力追趕國內其他友商,這三年對我們非常關鍵”,一位從大眾德國外派到合肥的華人工程師告訴汽車商業評論。
大眾集團2024年財報顯示,他們內部預測2025年和2026年仍將具有很大挑戰,在財務數字和銷量上不會很快有起色,他們預計回暖期在2027年。

